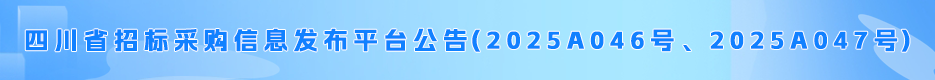政府采购是重要的公共财政管理手段,对市场具有较强的调控和引导作用。在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背景下,国务院办公厅去年印发《政府采购领域“整顿市场秩序、建设法规体系、促进产业发展”三年行动方案(2024—2026年)》,提出要进一步畅通权利救济渠道,做到“有诉必应”。但个别供应商却利用程序性权利来谋取不当利益,并呈现出专业化、隐蔽化趋势。
政府采购领域恶意投诉现状
恶意投诉认定标准缺失,处罚力度与违法收益倒挂。《政府采购质疑和投诉办法》(财政部令第94号,以下简称94号令)规定,投诉人有捏造事实、提供虚假材料、以非法手段取得证明材料等行为之一的,属于虚假、恶意投诉。但笔者认为,94号令对恶意投诉的定义不够清晰,构成要件也不够具体,使得基层对于恶意投诉的认定存在争议,间接造成处罚力度与违法收益倒挂。
目前,恶意投诉往往不涉及虚假材料,而是利用程序性瑕疵干扰采购进程,意图拖延项目、阻止竞争对手履约。比如,某公司为某地政府网络维护项目的原承建商,以新的中标人服务器“未完全符合GB/T 22239-2019”为由,在15天内连续5次发起投诉。经查,该标准为推荐性标准而非强制要求,但此举迫使采购人延长澄清期,不仅造成项目延期近3个月,而且使采购人额外支出澄清费用达12万元。
行政与司法衔接不畅,行业自律缺失。投诉人若不服行政主管部门判决,可向法院提出行政诉讼,主张撤销处罚。当前,针对政府采购投诉的诉讼案件中存在“同案不同判”的现象。换言之,行政与司法冲突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法律威慑力,助长了部分恶意投诉人的投机心理。比如,某医疗设备有限公司不服当地省财政厅对其恶意投诉的行政处罚,向2个市法院提起诉讼。N法院以“供应商在1年内3次投诉同类技术条款且均无证据,构成恶意投诉”为由支持处罚,S法院以“投诉理由虽不成立,但未发现伪造证据,处罚缺乏必要性”为由撤销处罚。笔者认为,虽然部分地方的政府采购协会制定了投诉行为指引,但也仅仅能采取通报批评、建议慎用等软性措施,导致行业自律作用未得到充分发挥。
技术防控体系建设滞后,部门数据互通存在壁垒。目前,我国尚未建立全国统一的政府采购投诉处理系统,各省市现有投诉受理系统对重复性、模板化投诉缺乏智能识别。个别省市虽然建设了政府采购投诉平台,但功能仅限于在线提交投诉案件等基础交互,无法发挥智能化甄别、筛选等功能。另外,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与政府采购投诉数据库尚未完全打通,数据推送存在延迟、错误等现象,无法及时触发预警系统。比如,某环保科技公司曾在2023年5月因虚假检测报告而被当地市场监管局处罚。同年8月,该企业在参与某市污水处理设备采购项目时,由于数据推送滞后,财政部门未能及时发现其关联风险。
加强恶意投诉管理的建议
明确恶意投诉认定标准。在94号令基础上,将主观要件设定为单次投诉涉及3项以上非实质性条款,或1年内发起同类投诉≥3次;客观要件设定为投诉事项经查证不成立且导致采购延误≥15个工作日,或3次以上投诉事项经查证不成立,同时投诉内容与采购结果存在直接关联的,判定为恶意投诉。同时,明确恶意投诉的司法认定规则,重点解决程序违法、实质损害、因果关系三大争议焦点。
创新协同治理机制。一是法院对高频投诉主体提起的诉讼实行实质审查前置,需提交第三方技术鉴定报告。二是设立阶梯式处罚机制。比如,对于首次轻微违规的,处以警告或书面告诫,1年内不得参与同类采购项目;对于1年内2次违规的,处以标的额1%—3%罚款,3年内限制其参与政府采购活动并列入失信名单。三是强化行业自律。鼓励行业协会对列入失信名单的企业实施“一票否决”,取消其参与行业评优资格。
构建智能防控系统。一是开发全国统一投诉监测平台,设置语义分析引擎(运用BERT模型识别模板化投诉文本,对重复提交相似内容的主体自动标记)、时间轴预警(对在法定期限临界点如开标前1日的集中投诉行为,实时弹窗提示)、关联图谱分析(分析投诉人股权结构,识别关联企业协同投诉行为),从而提升程序性投诉识别的准确率。二是打通跨部门数据接口,实现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、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与政府采购投诉数据库的实时共享,对失信方采取系统自动触发政府采购投诉风险预警,以便财政部门提前介入审查。
(作者:陈煜,作者单位:浙江省玉环市财政局)
来源:中国政府采购报第1470期第3版